余國琮:半世“精餾”夢,百年愛國情
2020年春日的一天,中國科學院院士、天津大學教授余國琮像往常一樣,在電腦前修改著書稿。書桌上放著一本夾著很多小紙條的《化工計算傳質學》,紙條上寫著這本書第三版的修訂內容。書下還壓著某國外知名科技出版公司發來的感謝信,感謝他提供了一本有水平且銷量好的科學專著。
就在這位98歲的老人享受春日暖陽之時, 4月24日,在第五個“中國航天日”和“東方紅一號”衛星成功發射50周年到來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給參與“東方紅一號”任務的老科學家回信的消息傳遍中華大地。信中,習近平總書記就弘揚“兩彈一星”精神、加快航天強國建設向廣大航天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
在人們的認知中,余國琮是我國精餾分離學科的創始人、現代工業精餾技術的先行者,以及化工分離工程科學的開拓者。但如果將時鐘撥回到半個世紀之前,我們就會發現,余國琮同樣為我國核技術的起步作出了寶貴貢獻。而他,也是“兩彈一星”精神的一生踐行者。
“回來,為自己的國家做點事”
1922年,余國琮出生于廣州西關。因日寇侵占廣州,他隨父母到香港避難,后考入西南聯大。戰火紛飛的年代和顛沛流離的生活,促使他在心底埋下了“科學救國、科學強國”的種子。
1943年,從西南聯大畢業后,余國琮赴美求學。1947年,博士畢業的余國琮成為匹茲堡大學化工系講師。短短一年后,他便被評為了助理教授。而此時,大洋彼岸的中國,解放戰爭臨近結束,余國琮的人生命運也將迎來一次巨大的轉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迎來了開國大典。僅一年后,余國琮便以到香港探親為由,毅然返回祖國。“很多人問我,為什么放棄美國那么好的工作、生活條件選擇回國,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那就是回來為自己的國家做點事。”在一篇自述中余國琮回憶道。
回國后的余國琮應邀到當時的唐山工學院組建化工系。1952年我國高校院系調整,該系并入天津大學。此后的半個多世紀,余國琮再沒有離開北洋園,在這里,他找到了自己為之奮斗一生的研究方向。
據余國琮的弟子、天津大學化工學院化學工程研究所所長袁希鋼介紹,上世紀50年代,我國的煉油工業剛剛起步,而蒸餾(也稱精餾)技術是其中的關鍵。余國琮敏銳地發現了這一產業重大需求,開始進行化工精餾技術領域的科研。
1954年,在他的指導下,我國第一套大型塔板實驗裝置正式建立。經過兩年的探索,余國琮于1956年撰寫的論文《關于蒸餾塔內液體流動阻力的研究》引起了當時化學工業部的注意,并被邀請參與化工部精餾塔標準化的大型實驗研究。此后不久,余國琮參與了我國第一個科學發展遠景規劃“十二年科技規劃”的制定工作。天津大學的化工“蒸餾”科研被列入十二年科技規劃之中,天津大學化學工程專業也于1958年設立。
此時,又一個歷史重擔壓到了余國琮的肩頭。
為了“爭一口氣”
就在天津大學化學工程專業設立的當年,我國由外國援建的首座原子反應堆投入運行。但由于國際關系突變,重水供應面臨中斷。開發我國自主的重水生產技術,成為了當時的國家重大需求。
就在這時,余國琮在天津大學展開的重水精餾分離技術研究進入國家視野。
1959年5月28日,周恩來總理來到天津大學,重點考察了余國琮所在的重水濃縮研究實驗室。“當時,周總理握著我的手說,現在有人要‘卡脖子’,不讓我們的反應堆運作。我們一定要爭一口氣,不能讓這個反應堆停下來。這句話我始終牢記。”為了“爭一口氣”,余國琮做研究時更加廢寢忘食了。
重水是原子裂變反應堆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資。在天然水中,重水的含量約萬分之一點五,如何將其提純到99.9%,并實現工業化生產?這是一項巨大的挑戰。為此,余國琮率領團隊,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日夜攻關,創造性地采用多個精餾塔級聯等多種創新的方式替代傳統的精餾方式。周恩來總理在視察實驗室一年之后,專門給學校打電話,詢問重水技術的研究進展。余國琮堅定地回復說:“可以告訴總理,研究進行得很順利。”
1965年,余國琮的多項成果和突破終于形成了我國自主重水生產工業技術,在原化工部配合下成功生產出了符合要求的重水,為新中國核技術起步提供了堅實的保障。重水分離技術的研制成功,也標志著我國的精密精餾技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我當初抱著樸素的愛國心回來,只想貢獻自己的一些力量。回國那年,我有幸參加天安門的國慶閱兵,也看到了偉大的解放軍。現在國家比當時強大了很多。我很高興為國家做了一點事情,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 提起關于重水的往事,余國琮十分欣慰。
從“技術”走向“科學”
在美國的學習經歷,讓余國琮對二戰后美國以及世界化工學科的發展趨勢有了深刻的了解。“‘戰后美國的化學工業發展得比較快,但中國人在基礎研究等多個領域仍有機會,我們有信心迎頭趕上。’余國琮先生曾這樣對我們說。”袁希鋼回憶道。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首批巨資引進的大慶油田原油穩定裝置是實現年利潤50億元乙烯生產的龍頭裝置。但是,由于裝置的設計沒有考慮我國原油的特殊性,投運后無法正常運行,整個流程都無法正常生產。外國技術人員數月攻關仍未解決這一問題。為此,余國琮應邀帶領團隊對該裝置展開研究,很快發現問題所在。經過運用自主技術對裝置實施改造,他們最終使整套裝置實現了正常生產,甚至一些技術指標還超過了原來的設計要求。
有專家表示,這次應用自主技術對工業裝置成功實施改造,開創了中國人給進口成套裝置“動手術”的先河,也為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科技工作者打破對進口技術的迷信樹立了信心。
進入21世紀,以大型石化工業為代表的化學工業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而精餾作為覆蓋所有石化工業的通用技術,在煉油、乙烯和其他大型化工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余國琮認識到,新的技術條件和市場需求,使現有的精餾技術不斷受到新的限制,特別是精餾在熱力學上的高度不可逆操作方式,以及在設計中對經驗的依賴,已經成為限制精餾技術進一步提高的瓶頸。
“工業技術的革命性突破必須在基礎理論和方法上取得突破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而基本理論和方法的突破必須要打破原有理論框架桎梏,引入并結合其他學科最新的理論和技術研究成果。”他說。
為此,余國琮針對精餾以及其他化工過程開辟了一個全新領域——化工計算傳質學理論。從根本上擺脫現有精餾過程工業設計中對經驗的依賴,讓化工過程設計從一門“技術”逐步走向科學,是這一新理論的明確目標,也是余國琮作為科學家的遠大目標。
“站著講課是我的職責”
如今已經是一所之長,但如果哪天有課,袁希鋼還是會凌晨4點起床,一遍遍審視講課內容。即使這門課他已經教授了多年、多次。“如此精益求精,就像精餾提純的過程,這是我對‘師者’身份的尊重。這份為人師表的使命擔當,則是余國琮先生傳遞給每個學生的寶貴財富。”袁希鋼說。
在大學校園度過了大半生的余國琮,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是一名人民教師,教書育人是我最大的職責。”
85歲那年,余國琮還堅持給本科生上一門“化學工程學科的發展與創新”的創新課。一堂課大約要持續3個小時,學生們怕先生身體吃不消,給他搬來了一把椅子,想讓他坐下來講。可余國琮卻總是拒絕:“我是一名教師,站著講課是我的職責。”
聽過余國琮課的人都說,“余先生把講課當成了一門藝術”。對于學生,余國琮有一份發自內心的喜愛。無論是國際上的前沿論壇、國內的學術交流,還是學校的各種科研活動,甚至是學生自發的科技活動,凡是接到邀請,只要時間和身體條件允許,他總會欣然接受。
曾有人問他為何如此拼命,余國琮回答說:“在國內外高水平論壇上的任務是交流,我們要把國外前沿的研究成果引進來,要把最新的研究成果推出去;科普工作則更為重要,為大學生講課是培養創新人才的重要途徑。只要身體條件允許,我能多講一些就多講一些,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投身祖國的化工事業,為祖國培養更多的優秀化工類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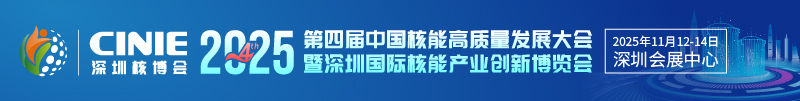

推薦閱讀
科學史上許多革命性的突破與發明常常充滿著神奇的偶然性,核磁共振(MRI)的發明就是有趣的一個例子。近十年來核醫學領域因PET MRI不斷裝機應用于臨床,為學科保持領先創造了奇跡。我們核醫學界對PET的發明發展應用熟稔在心,但對于MRI的發展歷史、特別是早期發展歷史,了解甚少。
2021-06-14
5月30日,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舉行學部第七屆學術年會全體院士學術報告會。中國科學院院士、光學專家李儒新發表了題為《高功率激光與高能粒子加速器融合前景廣闊》的演講,闡述了高功率激光和高能粒子加速器兩個不同的學科領域近年來相互促進交叉研究發展的有關情況。
2021-06-02
29日,日本《朝日新聞》發布了對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佩里的專訪內容。該專訪圍繞美國國防和核武器話題展開,佩里在受訪時表示,就目前的國際局勢來看,發生核戰爭或者核事故的可能性比冷戰時期還要高。
2021-06-01
NEA總干事麥格伍德評論道:“如果核工業錯過這場數字創新,那核能的未來將遭遇重大損失。”
2021-05-14
烏克蘭國家核監管檢查局委員會成員、核能問題專家奧莉加·科沙爾娜婭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指出,日本政府將福島第一核電站上百萬噸核污染水排入大海的決定堪稱“野蠻”行為,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物質將威脅人類健康。
2021-04-27
閱讀排行榜